校友风采
『校友风采第五期』1977级校友潘璠——选择母校,那是相当正确的
时间:2016-12-06 来源: 作者: 编辑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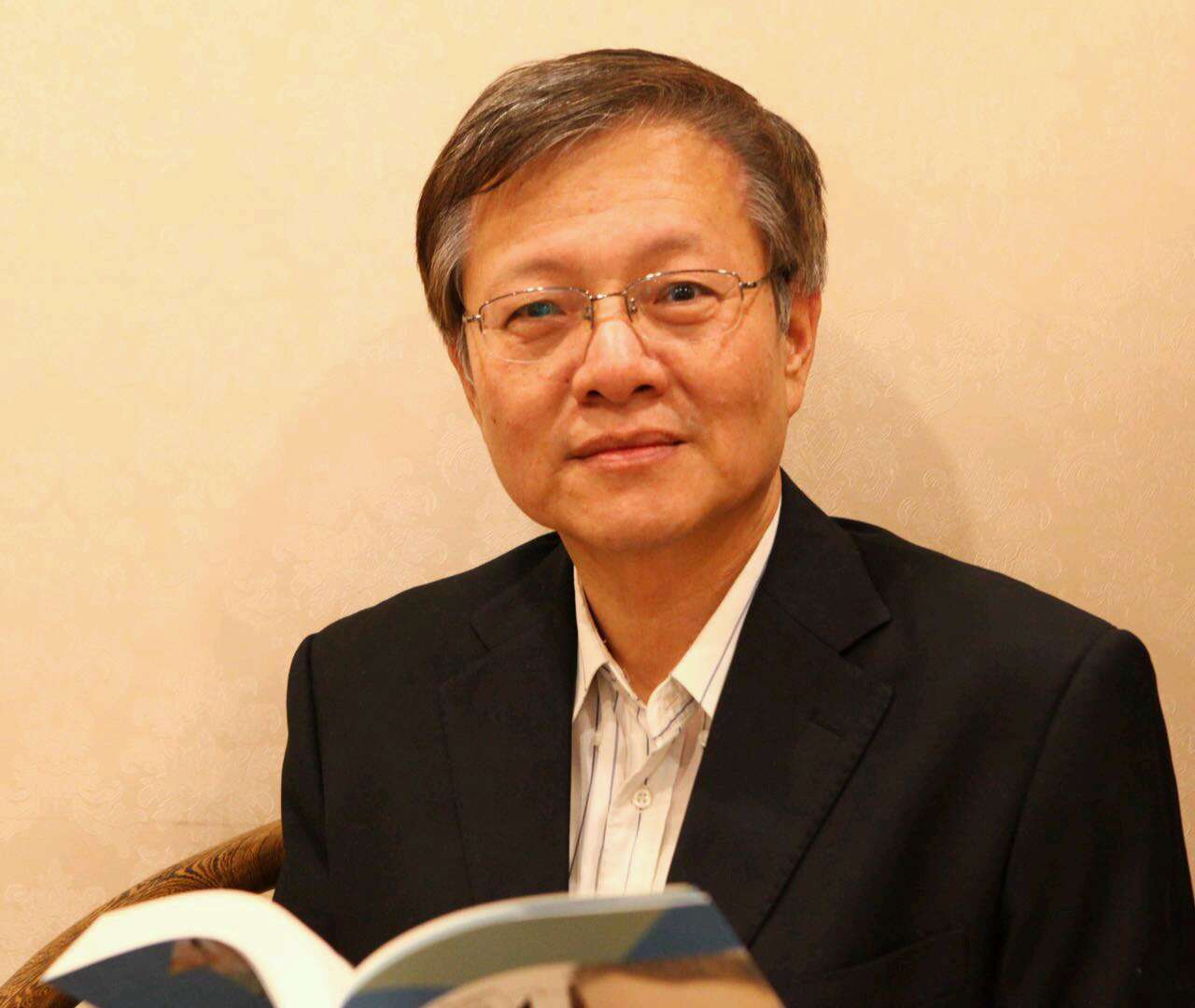
潘璠,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77级贸易经济专业校友,曾任北京金漆镶嵌厂工人, 1982年1月从北京经济学院(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前身之一)毕业,获经济学学士学位;1982年2月至2005年8月,在北京市统计局任科员至副局长,期间,获北京市委党校行政管理本科(第二)学历,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单考班在职研究生学历,经济学硕士;2005年8月至2011年7月,任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总队长,期间,获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;2011年7月至2014年12月,任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,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;2015年2月退休。
选择母校,那是相当正确的
—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77级校友、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潘璠自述
2008年10月18日,我们的母校举办了一场“纪念改革开放 77、78级校友入校30周年大会”。老汉我作为77级学生代表之一,也登台发表了几句感言。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说的:
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,可能要做许多次选择和决定。有的对了,有的错了。而我一生当中至少有一件事情,做得是相当正确的,那就是参加了高考,选择了北京经济学院。虽然今天,经济学理论的内容、方法及其实践、应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当年我们在母校得到的经济学的启蒙,确使我们、至少使我本人受益终身。
言为心声。老汉我说的,确实是真情实感。
1977:进校
我的小学、中学时期,正好赶上那场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ge命”。用侯宝林老先生的话说,那10年其实是“大革文化命”。除了停课,就是搞运动,学习的质量极差。初中毕业后我上了技校。虽然没有上高中,但我留下了一套课本,觉得早晚会用得着。
果然,进工厂没多久,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。白天,我在工厂“抓革命,促生产”,一天假也没有请。晚上,就钻进还没拆的抗震架子内,把头架在木头棱子上防止犯困,以恶补高中课本上的知识。时值寒冬,冷风呼啸,却正可以从漂着冰块的水缸中舀出冰水擦头,以驱赶不时光临的瞌睡虫。经过这样一番努力,终于拿到了北京经济学院财贸系贸易经济专业的录取通知书。有工厂内一起参加考试的工友说,也没见你小子请假复习,怎么考上的?俺回答:头悬梁锥刺股也!
为啥选择咱们经院呢?一是愿景期待。觉得国家百废待兴,学经济一定大有用武之地。二是从实际出发。短短几个晚上,要恶补高中阶段的全部数理化课程,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所以只能选择文科。文科中除了外语与师范类院校外,可选的院校、专业也实在有限。于是,这样一个选择,便注定了与母校结下的终身不解之缘。
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,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政治上“拨乱反正”、思想上百家争鸣、文化上百花齐放的一段复兴繁荣时期。这一阶段走进大学校园的我们,也正值风华正茂、意气风发的青春年华。于是,便也注定了我们在北京经济学院的四年,成为一生当中最轻松愉悦、最丰富多彩、最值得记忆与回味的一段快乐时光。有清晨操场上的奔跑,有傍晚阅览室中的抢座;有教室内的唇枪舌剑,有礼堂里的笑语欢声。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四年光阴转眼即逝,赵华风书记说,“经济学院的学生到经济部门工作,就是对口”。于是,在财贸系贸经专业学习了四年的我,就于1982年初毕业分配到了统计系统,一干就干到了退休。
1993:返校
走上工作岗位,一干十多年。因为公务繁忙,不仅从未想过再找机会深造,就是面对单位在职研究生的多次报名机会,也从没有动过心。直到1993年底的某一天,又一份报考在职硕士研究生班的通知让我眼前一亮,因为那个招生的学校正是我们的母校——北京经济学院。重回母校学习经济?这想法顿时让我心驰神往,下决心努一下、试一把。
虽然是市里组织的在职班,但毕竟要参加考试,且铁定要刷掉一半的考生。而老汉我那时身在机关,工作依然很紧张。于是,我的业余时间又调整到高考时复习备考那样的紧张状态。孩子送到老人那里,在家里煮了一锅牛肉,饿了就拿几块牛肉下一把面条,谓曰“潘氏牛肉面”。平时,拿两把小沙发对面一拼,人往里面一缩,又一门课一门课、一本书一本书地学习上了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在重回母校、学习经济的愿望激励下,凭着当年的经济学功底和毕业多年做经济工作的实践,我终于成为二分之一的幸运者,在1994年重新走进了红庙路口西南角那个熟悉的院落。虽然物是人非,但当年的教学楼、图书馆、宿舍楼、礼堂、食堂毕竟都依然如故,令人倍感亲切。而也就是与此前后,我们的母校改名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了。
2012:合作
自从获得硕士学位证书,再回母校参加各种活动,俺就往往要报三次到了。我们的贸经系(后来分成了经济学院和工商管理学院),要去;研究生处,也要去;还有就是统计学院了。人在统计系统工作,多年来与统计系及后来的统计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从丁立宏教授到纪宏教授,工作上的联系和学术上的交流真的非常频繁。而且,我在职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就是统计系的王持卫教授。所以俺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,都忘不了自己的统计身份。而在各种校方组织的活动之外,我如果走进母校的大门,还多一半跟统计有关。
这不是?2012年9月16日,老汉我走进了博学楼五层的一间会议室。丁立宏副校长在,纪宏院长也在。会议的主题就是聘请统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。为了培养专业硕士的实践能力,学院为他们每个人在聘请校内导师之外,还要再聘请一位兼职导师。这些兼职者都是校外人士,且大都是有实践经验的长者(仅相对于学生而言)。老汉我从事统计工作多年,也算是有一定实践经验吧;从年龄上说,当然更无愧长者称号,所以又光荣应聘。当然,这只是百分之一百地尽义务,分文不取。而老汉我则又将其视为跟母校的又一个缘分。
后来,李晓娜、崔路云两位同学成为俺的研究生,到俺所在的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实习。当时,我们研究所的头等“大”事,就是大数据的应用研究。俺安排她俩到经济统计研究室(后来改名为大数据研究室)参加研究。有些研究成果还印上了她们俩的大名。这也算是俺对母校做的一点点小贡献吧!
2015:回眸
2015年,是俺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。因为在这一年,我完成了从一个在职人员到退休人员的转变。虽然离开单位,依然置身社会。面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,有感而发,便溢于文字、泄于笔端。一年下来,不多不少,整整有一百篇文章见诸于纸媒。其实呢,这不过是多年形成的一种常态而已。
也记不准从啥时候起,爬格子就成了俺业余时间里的一种生活方式。从没有想在哪个领域整出啥名堂,所以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,只是笔随心走,随心所欲;想哪说哪,想啥说啥。专业论文、时评、随笔、杂文、影评、散文等等,形式各异,内容庞杂。所以,俺自嘲说是写统计论文的人里面还写经济评论的,写经济评论的人里面还写电影评论的,写电影评论的人里面还写时事评论的,写时事评论的人里面还写统计论文的。仅新世纪以来,俺就有一千多篇文章、上百万的文字见诸报端。而这些或长或短的文字中,有些许分量的,多数还是与专业有关的东东。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头的那句话,当年在母校得到的经济学的启蒙,真的使我终生受益。
1992年11月,《人民日报》理论部举办征文,俺的一篇《改革需要实践》见报并获三等奖第一名。虽然与预期有差距,但一看获奖名单,特等奖邹家华、李铁映、张劲夫,一等奖贾庆林等,俺也就觉得能获奖就不错了。
2013年7月,一位著名企业家发声,劝年轻人别急着买房。老汉我虽早已过半百,但也是年轻人的老爸,个中甘苦自有所体会,所以设身处地、感同身受地写了一篇《年轻人为啥急着买房》。在《中国青年报》见报后,包丽敏老师发来邮件称,有755家网站转载,在中青报一周所有稿件中位居第三。“可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,很难让这些转载网站都支付稿费。”呵呵,没稿酬没关系,得到认可就好。
2014年5月初,有政府部门官员提出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跨入“中高国家行列”,在社会上引发较强质疑,《经济日报》希望我写一篇理性分析文章。于是,一篇《我国人均GDP质量确需提升》刊发于5版头条“正本清源理性看”专栏。新浪网主页在“新闻”和“猜你喜欢”两个栏目同时显示出来。时至今日,如果在百度搜一搜“房价严重背离价值”、“大多数人收入被少数人平均”等表述,多数都是俺那篇及以后的相关文章。当然,价值也好,价格也罢,都是俺在母校学习时初识的概念。
同年6月20日,下了班天依然很亮,我正准备去继续走遍京城每一条胡同。《经济日报》的杨开新小杨老师打来电话,说国家领导人近期参加国际活动时多次讲中国有信心完成7.5%的全年目标,而有媒体过度解读说“即使7.49也是没完成”,因此需要写一篇文章回应和解读,当晚10时就要交稿。于是,老汉我放弃逛胡同的计划,赶紧回家,按时完成了任务。第二天,一篇《不要把7.5%当作一个“绝对数”》的文章见诸于该报头版。小杨后来说,该文当天上了中国政府网的要闻位置,与领导人出访消息排在一起,国办领导对此表示感谢。而老汉我知道,俺这点儿功底,也还是在母校时打下的。
与母校的话题总是说不完的。这不,我们的母校就要迎来第一个60周年校庆。有第一就有第二。希望下一个花甲之时,我们这些校友还能一起庆祝和纪念。希望我们研究生班的校友、现校友会的喜玲秘书长,到时候想着招呼一声。


